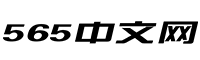分节阅读_45(1/2)
作者:叶子
商者来说,“急”需的援助价值之高,可能超过正常使用的几倍或几十倍,有时甚至 体现出再造生命的价值。当“危机”一过,便会有困难中见真情的“难友”或“恩人”。许 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是这些关键时刻建立起来的,从这个义意上讲,钱还能促进人与人之 间感情的进化和升华。
谁都知道,钱,是人们赖以商品交换的等值物,放在银行里还能增值,若是投资做生意 ,还会像鸡蛋生小鸡那样不断倍增。如果你赔了,说明你的市场判断有误或缺乏某种经营能 力,但若是以此作为无限期的拖延或不还债的理由,那你苦心经营的信誉市场可能已近风中 残烛,也很难有东山再起的希望。如今,有许多人本想借鸡生蛋,结果连鸡也赔上,从此一 蹶不振再也没有能力也不想去补求了。对于上门讨债者,他或者一副“爷爷”之态,除了一 再回避,就是编故事,骗得“孙子”跑了一趟又一趟,或者采用无赖汉的哲学,任凭你怎样 “跑断腿磨破嘴”,他是硬的不吃软的不进,“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就是由于这些人,为债务问题闹上法庭的事例举不胜举。讨债者人证物证俱在,说得声 色并茂理直气壮;欠债者却像霜打过的菜叶,一副穷途末路的可怜状,你判刑也好,坐牢也 罢,他反正是听天由命了。这就使许多讨债者因耗不起大量的时间和心力,而使之成为无期 的“死债”。有此前车之鉴,便接受其教训,以后宁愿让钱闲置在家,也“见死不救”,省 得麻烦。
假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种心态,先不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冷暖关系,就商品经济的 运转和资金的利用而言,也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不能不说是社会发展的一大人为的悲哀。
当然,对于尽了最大努力仍还不起债的“杨白劳”来说,自己也并不好过,自古有“吃 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欠人家的理短”的俗训,谁愿意背着“理短”做人呢?但这里 有个态度和协商的弹性问题,如果你主动协商态度诚恳,有赚钱的拼搏决心,相信“黄世仁 ”会给予理解和宽限的。但如果“黄世仁”还欠了别人的债,形成了三角债关系,你就应该 积极想办法换个债主,借用“拆了西墙补东墙”的缓解办法,按约还债。这不仅仅是你个人 的信誉问题,更是一种维护社会公德的义务。
无论是大生意,还是小周转,只要有了相互信任,自觉遵守合约的良好信誉环境,自然 会有更多的“救急”资金。有了资金,就有了效益的命脉,不仅有利于个人,更有利于社会 的经济发展。这样,“黄世仁和杨白劳”与“爷爷和孙子”的关系,将变为相互帮助、互惠 互利的礼尚往来关系,也许还因为相互扶持产生永恒的友情、恩情关系。
悠着点“炒”,慢着点“跳”
“炒鱿鱼”和“跳槽”都是时代的新名词,尤其是在广东这块热土,机制灵活,“炒” 或“跳”无论是哪方的原因,人员的流动都是正常的事。本来这是个优点,让双方都能有更 好的人选和机会,但如果人员的流动像走马灯一样过于频繁,就不得不让人觉得“浮躁”了 。现在,就有一些被浓重的商品味熏得头脑发涨的老板和打工族们,越来越找不到“对胃口 ”的感觉了。再招聘、再求职的高速运转在同一些供需之间轮回,人员流动的“超高”和衔 接不当造成的混乱及经济损失,不能不说是双方都缺乏某种谐调素质使然。
谈“炒”者
一个稳定而有生机的企业,必定有一个会用人的老板,他会因人的个性、特长,而慎重 取舍职员们固有的优劣之处。据说,西方国家一些大的老牌企业,有半数以上的职员自愿终 生效力,而凭他们高水平的技术和业务能力,足够“自立门户”或跳糟别处拿更高的薪金。 究其原因,不外乎老板德才兼备、仁厚待人,使下属们不“为知己者死”,便有背叛苍天之 感。
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有的老板不是以企业的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对那些识大体、有实 干和敬业精神的员工按劳取酬,长期任用,而是有些聪明过头,总想赚员工们的“试用期工 资”的小便宜,等三个月的试用期已满,便巧立名目不给长工资。一副“有食不怕引不来鸟 ”的态度:“你若嫌钱少,可以走人”。
另一种老板是靠机遇而一时发际,然后模仿别人办公司搞企业,不管几个人的规模,“ 大小也是个老板”,是老板就要端一端老板的架子,就要感受到人上人的优越,耍耍老板的 威风:“我是老板,我说了算,你他妈的不服?我炒了你。”
像这样素质的老板,这样老板的企业,会有怎样的形象和发展前景呢?
论“跳”者
自古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大实话,这里不是指视觉上的“欲穷千里目,更 上一层楼”,而是指生活中的官本位、钱本位、物本位。对于这些勇于“登高”者,本也无 可厚非,但这个“高度”一旦掌握不好,便会把自己摔得变形,“跳糟族”里就不乏其例。
就说一个层次高一点的本科生吧,抛开内陆按部就班的死板和层层关系的束缚,怀着满 腔热血来到这块开发区寻找用武之地。果然,一纸大本文凭像万能钥匙一样,一次次地把招 贤纳士的企业大门启开,这里灵活的老板给了他许多选择的机会。但是,经济效益第一的严 酷性和紧迫感,又使得他在哪里都觉得不尽人意。不是老板的苛刻伤了自尊,就是工作的繁 琐不堪重负,抑或是环境差报酬低,心理找不到平衡。开始是不好意思跳槽,后来是不在乎 跳槽,继而少不顺心就想跳槽。几经反复,他变得像个滑了丝的螺丝钉,扭到哪里也失去 了原态。结果,不但没有登上理想的“高度”,反而把原有的热情和自负,消耗在许多叹息 之中。
类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他们的“不得志”绝对不是没遇上伯乐或怀才不遇,人总要 适应环境,而不是要求环境来适应自己,不是吗?
当然,老板如果不沙里淘金炒掉那些滥竽充数的人,也不是好老板;有大作为的人而一 味地坚持“忠臣不保二主”的高尚传统,也并不可取。但是,大部分人都有一定的共性,如 果每个人都多一些宽容和自我调
谁都知道,钱,是人们赖以商品交换的等值物,放在银行里还能增值,若是投资做生意 ,还会像鸡蛋生小鸡那样不断倍增。如果你赔了,说明你的市场判断有误或缺乏某种经营能 力,但若是以此作为无限期的拖延或不还债的理由,那你苦心经营的信誉市场可能已近风中 残烛,也很难有东山再起的希望。如今,有许多人本想借鸡生蛋,结果连鸡也赔上,从此一 蹶不振再也没有能力也不想去补求了。对于上门讨债者,他或者一副“爷爷”之态,除了一 再回避,就是编故事,骗得“孙子”跑了一趟又一趟,或者采用无赖汉的哲学,任凭你怎样 “跑断腿磨破嘴”,他是硬的不吃软的不进,“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就是由于这些人,为债务问题闹上法庭的事例举不胜举。讨债者人证物证俱在,说得声 色并茂理直气壮;欠债者却像霜打过的菜叶,一副穷途末路的可怜状,你判刑也好,坐牢也 罢,他反正是听天由命了。这就使许多讨债者因耗不起大量的时间和心力,而使之成为无期 的“死债”。有此前车之鉴,便接受其教训,以后宁愿让钱闲置在家,也“见死不救”,省 得麻烦。
假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种心态,先不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冷暖关系,就商品经济的 运转和资金的利用而言,也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不能不说是社会发展的一大人为的悲哀。
当然,对于尽了最大努力仍还不起债的“杨白劳”来说,自己也并不好过,自古有“吃 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欠人家的理短”的俗训,谁愿意背着“理短”做人呢?但这里 有个态度和协商的弹性问题,如果你主动协商态度诚恳,有赚钱的拼搏决心,相信“黄世仁 ”会给予理解和宽限的。但如果“黄世仁”还欠了别人的债,形成了三角债关系,你就应该 积极想办法换个债主,借用“拆了西墙补东墙”的缓解办法,按约还债。这不仅仅是你个人 的信誉问题,更是一种维护社会公德的义务。
无论是大生意,还是小周转,只要有了相互信任,自觉遵守合约的良好信誉环境,自然 会有更多的“救急”资金。有了资金,就有了效益的命脉,不仅有利于个人,更有利于社会 的经济发展。这样,“黄世仁和杨白劳”与“爷爷和孙子”的关系,将变为相互帮助、互惠 互利的礼尚往来关系,也许还因为相互扶持产生永恒的友情、恩情关系。
悠着点“炒”,慢着点“跳”
“炒鱿鱼”和“跳槽”都是时代的新名词,尤其是在广东这块热土,机制灵活,“炒” 或“跳”无论是哪方的原因,人员的流动都是正常的事。本来这是个优点,让双方都能有更 好的人选和机会,但如果人员的流动像走马灯一样过于频繁,就不得不让人觉得“浮躁”了 。现在,就有一些被浓重的商品味熏得头脑发涨的老板和打工族们,越来越找不到“对胃口 ”的感觉了。再招聘、再求职的高速运转在同一些供需之间轮回,人员流动的“超高”和衔 接不当造成的混乱及经济损失,不能不说是双方都缺乏某种谐调素质使然。
谈“炒”者
一个稳定而有生机的企业,必定有一个会用人的老板,他会因人的个性、特长,而慎重 取舍职员们固有的优劣之处。据说,西方国家一些大的老牌企业,有半数以上的职员自愿终 生效力,而凭他们高水平的技术和业务能力,足够“自立门户”或跳糟别处拿更高的薪金。 究其原因,不外乎老板德才兼备、仁厚待人,使下属们不“为知己者死”,便有背叛苍天之 感。
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有的老板不是以企业的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对那些识大体、有实 干和敬业精神的员工按劳取酬,长期任用,而是有些聪明过头,总想赚员工们的“试用期工 资”的小便宜,等三个月的试用期已满,便巧立名目不给长工资。一副“有食不怕引不来鸟 ”的态度:“你若嫌钱少,可以走人”。
另一种老板是靠机遇而一时发际,然后模仿别人办公司搞企业,不管几个人的规模,“ 大小也是个老板”,是老板就要端一端老板的架子,就要感受到人上人的优越,耍耍老板的 威风:“我是老板,我说了算,你他妈的不服?我炒了你。”
像这样素质的老板,这样老板的企业,会有怎样的形象和发展前景呢?
论“跳”者
自古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大实话,这里不是指视觉上的“欲穷千里目,更 上一层楼”,而是指生活中的官本位、钱本位、物本位。对于这些勇于“登高”者,本也无 可厚非,但这个“高度”一旦掌握不好,便会把自己摔得变形,“跳糟族”里就不乏其例。
就说一个层次高一点的本科生吧,抛开内陆按部就班的死板和层层关系的束缚,怀着满 腔热血来到这块开发区寻找用武之地。果然,一纸大本文凭像万能钥匙一样,一次次地把招 贤纳士的企业大门启开,这里灵活的老板给了他许多选择的机会。但是,经济效益第一的严 酷性和紧迫感,又使得他在哪里都觉得不尽人意。不是老板的苛刻伤了自尊,就是工作的繁 琐不堪重负,抑或是环境差报酬低,心理找不到平衡。开始是不好意思跳槽,后来是不在乎 跳槽,继而少不顺心就想跳槽。几经反复,他变得像个滑了丝的螺丝钉,扭到哪里也失去 了原态。结果,不但没有登上理想的“高度”,反而把原有的热情和自负,消耗在许多叹息 之中。
类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他们的“不得志”绝对不是没遇上伯乐或怀才不遇,人总要 适应环境,而不是要求环境来适应自己,不是吗?
当然,老板如果不沙里淘金炒掉那些滥竽充数的人,也不是好老板;有大作为的人而一 味地坚持“忠臣不保二主”的高尚传统,也并不可取。但是,大部分人都有一定的共性,如 果每个人都多一些宽容和自我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