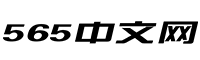分节阅读_39(1/2)
作者:叶子
的妈妈,吃的穿的可以每天像过年一样好了。但是,对年的期盼和感情却麻木了,甚至越 来越疏淡,越来越有些不耐烦了。经常觉得才过了年不久,年又要到来,年的频率过高,让 人感觉紧张和沉重,大有被年所累之感。
那时候的年,是作为孩子可以看鞭炮,包饺子,嗑瓜子,手舞足蹈蹦蹦跳跳,开心了就 哈哈大笑,受了委屈就嚎淘大哭,无论你怎样任性,人们总把你当成孩子,予以宽容和忍让 。后来,渐渐地人们开始对你客气,尊称你为大“姐姐”,好像在提醒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要注意自己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要树立一个大人的形象,完善大人应有的修养。再后来 ,就有人尊称你为“阿姨”,你也当了母亲。这时,就开始渐渐忘却自己,孩子成了主题, 为她ca心一日三餐衣食住行,该吃饭了该穿衣了,该上学了,别冻着热着,还要洗衣服搞卫 生,常忙得自己忘了洗脸梳头。更重要的是,仍然需要工作,需要挣钱养家糊口,做人的负 担使你忽略了许多,却不知是什么。
这时,年的到来会让你感到突然和意外,你会猛然发现对年的粗心大意,发现多年来期 盼的大好青春和美丽故事被忽略了。像一场梦,似曾经历过,却朦朦胧胧,那些人生最美好 的年华和失不再来的珍贵的“年”,已经在你无意间流失了。年,对你已成了一个人生的符 号,成了春夏秋冬轮回的钟点,你不会再为之期盼,为之激动和兴奋了。年,成了孩子们期 盼的故事。
前几年,在南方工作,为了女儿,每年都要飞回来过年。每次回来,女儿总是欢快得像只小 鸟,又蹦又跳,逢人就炫耀:“我妈妈回来了,我妈妈回来了”!每当我要离开时,她总是 反复地问“还有多少天就过年?你提前几天回来?”刚过完年就在为下一个年的到来数指头 了,这是多么真切而生动的接力棒啊!
这难道就是过年的积累和过年的意义所在吗?“过年”,对孩子们意味着欢乐与满足,但对 父母们无疑是一种越来越沉重的负担!
怀念外婆
外婆离开了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而我却没有参加她的葬礼,当我在大海彼岸的另一个 国度通过越洋电话得知她去世的消息时,她已经去世好几天了。一直想为她好好地尽孝道的 我永远没有机会了,这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这么多年来,如果不是逢年过节,我几乎已经忘记远在千里之外的外婆了。她连名字都 没有,可谓是孔夫子思想的典型代表,三从四德,循规蹈矩,十几岁就嫁给了外公,除户籍 档案上把外公的姓后加了个“氏”字为她的名字用过外,再也没有人需要或用过她的姓氏。 她认为有没有名字都一样,生儿育女做针线活才是女人真正的立命之本。
我从一岁多刚断奶就常住在外婆家,我是她最大的孙辈人,享受着她对另一代人最多的 亲爱情怀。她会把自己碗里的肉夹到我碗里,会悄悄地从大襟衣袋里掏给我半块糖果,会等 家里无人时给我两页饼干或一角苹果。因此,到上小学五年级了我还是经常去住下,一听要 到姥姥家,总会连蹦带跳,高兴得撒欢。
在我的记忆里,外婆似乎没睡过一宿囫囵觉,我晚上醒来,她不是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 ,便是披着月光在院子里理顺收回的庄稼之类的东西。最让我铭记的是,往往还在睡梦中就 被她那“咕哒咕哒”的做饭风箱声唤醒,睁眼一看,天才朦朦亮。如果碰上年节,她就更忙 了,提前好几个月就开始忙穿的吃的,整宿不睡,眼睛常熬得血红。忙完她家的,还要步行 十里路到我家帮我母亲忙活,我家孩子多,那活干开了更是没头没尾,她经常是早晨天不亮 就来,晚上再摸着黑赶回去,恨不能把自己分成两半。
外婆没上过学,虽然“女子无才便是德”在她思想上根深蒂固,但自我上学后,她常让 我给她讲学过的课文,她听得津津有味,却不知道我讲的对错,这常使我不懂装懂混水摸鱼 ,有时我还会顺着课文续编故事,编得头尾相适有声有色,连我都不相信是自己编的。如果 那时就开始写东西,凭那丰富的想象力一定能写出不少精彩的小说。
那时我就跟外婆说:“长大了我养着你,天天给你讲故事”,即使后来结婚了,我也想跟她 生活在一起,等她老了我就赡养她。可事与愿违,多少年来,每次去接她,她都是“舍不得 那个家”,无论我怎样争取,就是无法改变她的观念。
最后一次见到外婆是十多年前了,那时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她从农村接出来,她说我有丈夫有 小孩子的不方便,外孙女家不是女儿家,不能说去住就随便去住,“你心里没什么,你丈夫 会怎么想呢?”但她还是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最终答应来青岛小住,我为有这个亲近和赡 养她的机会惊喜和欣慰。
外婆在我家显得很拘谨,一惯劳劳碌碌的她,很想帮我做些家务,却又无处下手,有时站也 不是坐也不是无所适从,只有那灰暗的有些呆板的眼神,跟随我出出进进,一刻也离不开, 仿佛要从我身上找出些什么。我猜想她一定也觉得我变得陌生了,那个依偎在她怀里撒娇要 这要那的小女孩,怎么变得很遥远很不可琢磨了呢?看到她孤寂难于闲度的样子,我经不住 她的再三要求,只好找出该拆洗的棉衣,让她拆洗了再做起了,使她的时间有所寄托。
外婆真如她自己所说,已经老得“不中用了”。吃饭时,她布满清筋的不停地颤抖的手 ,无论她怎样努力,也无法避免碗筷随着颤抖发出的碰撞声,我看得出,即使我们都装得 什么也没听见,这声音也使她在我丈夫面前很难堪。尤其我那不懂事的女儿,像见了怪物一 样直盯着看,好奇地连饭也顾不得吃。当然,还有外婆那没牙的嘴,每次吃饭,简直就成了 女儿百看不厌的风景。
外婆嘴里本来还有两颗好牙,但没法“配对”,每次做饭我就犯愁,绞尽脑汁做的饭菜 她也无法下肚,只能用牙床吃点鸡蛋豆腐之类的食物。当我下定决心要给她镶牙时,她却提 出要回老家,并小心翼翼地从那个小时候给我装糖果的大襟衣袋里掏出一百元钱,里三层外 三层地用手帕包着,使我如同看到鲁迅的《药》里那个血馒头,她说这钱是我以前给她“买 好东西吃的”
那时候的年,是作为孩子可以看鞭炮,包饺子,嗑瓜子,手舞足蹈蹦蹦跳跳,开心了就 哈哈大笑,受了委屈就嚎淘大哭,无论你怎样任性,人们总把你当成孩子,予以宽容和忍让 。后来,渐渐地人们开始对你客气,尊称你为大“姐姐”,好像在提醒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要注意自己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要树立一个大人的形象,完善大人应有的修养。再后来 ,就有人尊称你为“阿姨”,你也当了母亲。这时,就开始渐渐忘却自己,孩子成了主题, 为她ca心一日三餐衣食住行,该吃饭了该穿衣了,该上学了,别冻着热着,还要洗衣服搞卫 生,常忙得自己忘了洗脸梳头。更重要的是,仍然需要工作,需要挣钱养家糊口,做人的负 担使你忽略了许多,却不知是什么。
这时,年的到来会让你感到突然和意外,你会猛然发现对年的粗心大意,发现多年来期 盼的大好青春和美丽故事被忽略了。像一场梦,似曾经历过,却朦朦胧胧,那些人生最美好 的年华和失不再来的珍贵的“年”,已经在你无意间流失了。年,对你已成了一个人生的符 号,成了春夏秋冬轮回的钟点,你不会再为之期盼,为之激动和兴奋了。年,成了孩子们期 盼的故事。
前几年,在南方工作,为了女儿,每年都要飞回来过年。每次回来,女儿总是欢快得像只小 鸟,又蹦又跳,逢人就炫耀:“我妈妈回来了,我妈妈回来了”!每当我要离开时,她总是 反复地问“还有多少天就过年?你提前几天回来?”刚过完年就在为下一个年的到来数指头 了,这是多么真切而生动的接力棒啊!
这难道就是过年的积累和过年的意义所在吗?“过年”,对孩子们意味着欢乐与满足,但对 父母们无疑是一种越来越沉重的负担!
怀念外婆
外婆离开了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而我却没有参加她的葬礼,当我在大海彼岸的另一个 国度通过越洋电话得知她去世的消息时,她已经去世好几天了。一直想为她好好地尽孝道的 我永远没有机会了,这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这么多年来,如果不是逢年过节,我几乎已经忘记远在千里之外的外婆了。她连名字都 没有,可谓是孔夫子思想的典型代表,三从四德,循规蹈矩,十几岁就嫁给了外公,除户籍 档案上把外公的姓后加了个“氏”字为她的名字用过外,再也没有人需要或用过她的姓氏。 她认为有没有名字都一样,生儿育女做针线活才是女人真正的立命之本。
我从一岁多刚断奶就常住在外婆家,我是她最大的孙辈人,享受着她对另一代人最多的 亲爱情怀。她会把自己碗里的肉夹到我碗里,会悄悄地从大襟衣袋里掏给我半块糖果,会等 家里无人时给我两页饼干或一角苹果。因此,到上小学五年级了我还是经常去住下,一听要 到姥姥家,总会连蹦带跳,高兴得撒欢。
在我的记忆里,外婆似乎没睡过一宿囫囵觉,我晚上醒来,她不是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 ,便是披着月光在院子里理顺收回的庄稼之类的东西。最让我铭记的是,往往还在睡梦中就 被她那“咕哒咕哒”的做饭风箱声唤醒,睁眼一看,天才朦朦亮。如果碰上年节,她就更忙 了,提前好几个月就开始忙穿的吃的,整宿不睡,眼睛常熬得血红。忙完她家的,还要步行 十里路到我家帮我母亲忙活,我家孩子多,那活干开了更是没头没尾,她经常是早晨天不亮 就来,晚上再摸着黑赶回去,恨不能把自己分成两半。
外婆没上过学,虽然“女子无才便是德”在她思想上根深蒂固,但自我上学后,她常让 我给她讲学过的课文,她听得津津有味,却不知道我讲的对错,这常使我不懂装懂混水摸鱼 ,有时我还会顺着课文续编故事,编得头尾相适有声有色,连我都不相信是自己编的。如果 那时就开始写东西,凭那丰富的想象力一定能写出不少精彩的小说。
那时我就跟外婆说:“长大了我养着你,天天给你讲故事”,即使后来结婚了,我也想跟她 生活在一起,等她老了我就赡养她。可事与愿违,多少年来,每次去接她,她都是“舍不得 那个家”,无论我怎样争取,就是无法改变她的观念。
最后一次见到外婆是十多年前了,那时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她从农村接出来,她说我有丈夫有 小孩子的不方便,外孙女家不是女儿家,不能说去住就随便去住,“你心里没什么,你丈夫 会怎么想呢?”但她还是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最终答应来青岛小住,我为有这个亲近和赡 养她的机会惊喜和欣慰。
外婆在我家显得很拘谨,一惯劳劳碌碌的她,很想帮我做些家务,却又无处下手,有时站也 不是坐也不是无所适从,只有那灰暗的有些呆板的眼神,跟随我出出进进,一刻也离不开, 仿佛要从我身上找出些什么。我猜想她一定也觉得我变得陌生了,那个依偎在她怀里撒娇要 这要那的小女孩,怎么变得很遥远很不可琢磨了呢?看到她孤寂难于闲度的样子,我经不住 她的再三要求,只好找出该拆洗的棉衣,让她拆洗了再做起了,使她的时间有所寄托。
外婆真如她自己所说,已经老得“不中用了”。吃饭时,她布满清筋的不停地颤抖的手 ,无论她怎样努力,也无法避免碗筷随着颤抖发出的碰撞声,我看得出,即使我们都装得 什么也没听见,这声音也使她在我丈夫面前很难堪。尤其我那不懂事的女儿,像见了怪物一 样直盯着看,好奇地连饭也顾不得吃。当然,还有外婆那没牙的嘴,每次吃饭,简直就成了 女儿百看不厌的风景。
外婆嘴里本来还有两颗好牙,但没法“配对”,每次做饭我就犯愁,绞尽脑汁做的饭菜 她也无法下肚,只能用牙床吃点鸡蛋豆腐之类的食物。当我下定决心要给她镶牙时,她却提 出要回老家,并小心翼翼地从那个小时候给我装糖果的大襟衣袋里掏出一百元钱,里三层外 三层地用手帕包着,使我如同看到鲁迅的《药》里那个血馒头,她说这钱是我以前给她“买 好东西吃的”